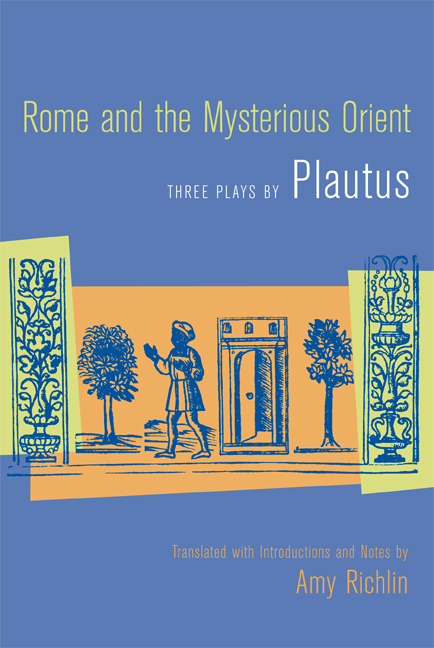表演入场
《受到召唤:敦煌》与罗马哑剧
似乎,在近现代戏剧发展史上,以观看明星演唱会的方式来观看一部严肃的历史文化题材的话剧实属罕见。但在古代罗马帝国,这却是占据罗马剧场最重要地位的娱乐舞蹈——罗马哑剧——的常态。罗马哑剧是拥有粉丝群体的舞蹈艺人以独舞方式表现古希腊悲剧和神话故事的表演。对此,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剧场文化中心叙利亚安条克的演说家利巴尼乌斯(Libanius)这样论述:
“直到悲剧作家群体的高峰时期,他们是参与剧场的民众的公共教师。然而,当其过了高峰期之后,在博物馆里接受教育成为有钱有权者们的特权,而大多数人被剥夺了这一权利。有一位神明怜悯大众没有教养,于是作为替代,介绍了哑剧舞者作为大众关于古昔之事的教师。因此,现在,一名金匠勉强可以与接受正规教育者谈论关于普里阿莫斯与拉伊俄斯家庭之事。”(《演说词》第64篇,第112节)
按照利巴尼乌斯的记载,在古典希腊时期,悲剧是公民教化的主要方式。但到了希腊化之后,悲剧衰落,教育为精英群体占有,到了罗马帝国时期,有声的希腊悲剧被改造成无声的舞蹈哑剧,民众再次得以接触古希腊文化遗产,进而金匠也可以和接受了正规教育者谈论荷马史诗的故事(普里阿莫斯代表《伊利亚特》、拉伊俄斯代表《奥德赛》)。那么化用利巴尼乌斯的话,或许可以说,在人文学科越来越被看作只适合少数有闲有钱者学习的“天坑”专业的今天,张艺兴的话剧让众多大中小学阶段的粉丝得以了解敦煌的基本历史和与敦煌学相关的学术史,让普通人也可以与历史专业研究生讨论常书鸿与陈寅恪之事。
不过,尽管利巴尼乌斯这篇演说词里对罗马哑剧评价很高,但这并不是罗马帝国时期主流知识精英们的态度。利巴尼乌斯这篇演说词意在反驳其知识偶像、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希腊知识精英领袖阿里乌斯·阿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的观点,后者认为哑剧舞蹈伤风败俗。阿里斯提德斯这篇批评哑剧舞蹈的演说没有完整流传下来,但根据利巴尼乌斯引用的部分段落,仍能窥见阿里斯提德斯的演说里充斥的对哑剧舞蹈性别化的偏见,因为在公元2世纪,哑剧舞蹈的基本特点是所有舞者都是男性,女性角色也由男性扮演。
和阿里斯提德斯大约同时期、与利巴尼乌斯一样来自叙利亚的希腊语作家琉善(周作人译为路吉阿诺斯)同样记载了反对罗马哑剧的声音,其关于哑剧舞蹈的系统论述《论舞蹈》以这样一个经典场景开篇:
“卢西努斯啊,你是这样一个君子,在博雅教育熏习下成长,对哲学亦有涉猎,却偏离了追求更善之事,不去与古人们对话,而坐在那响着双笛之音的(剧院里),看着穿着细软的娘炮在那浸透在靡靡之音中模仿性感女子们(起舞),呈现的都是些那些史上最淫荡的女子们,比如费德拉、帕尔特诺怕、罗多帕之流。而所有的这些都与弦乐声、笛鸣声以及脚步蹦跶声相伴。这真是彻头彻尾的可笑之事,最与你这样的自由男性地位不搭。而在我看来,当你沉迷在这样的表演中时,我不仅为你感到羞耻,还感到悲伤,当你坐在(剧院里),与那些为满足耳朵之欲(直译:用羽毛给耳朵瘙痒)之流为伍有相同体验之时,你已经忘记了柏拉图、克里斯普斯与亚里士多德。”(琉善《论舞蹈》第2节)
上述段落作为犬儒派哲学家的克拉通(Craton)的开场白,对哑剧舞者的性别化攻击非常明显,也强调像卢西努斯(Lycinus,琉善对话里经常出现的人物)这样有教养的知识精英,不应该去剧场里和拍手狂欢的女性粉丝群体共同观看有着女性化气质的男性舞者表演。紧接着,卢西努斯进行了长篇辩护,强调哑剧舞蹈承载的是古希腊文化遗产,只是不同于希腊智者长篇记诵大量希腊经典,哑剧舞者动用身体机能,用身体记忆呈现古希腊悲剧神话的故事情节,因而哑剧舞者和希腊智者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最后,克拉通被卢西努斯的长篇论述说服,叫他下次去看哑剧不要忘了带上他。
洛杉矶加州大学罗马喜剧研究学者艾米·瑞赤琳(Amy Richlin)把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喜剧家普劳图斯(Plautus)的喜剧剧本进行现代化翻译。她将共和国罗马的场景置入当代洛杉矶,用美国社会生活逻辑对喜剧里呈现的古罗马生活进行再次演绎。类似的,如果我们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生态去对《论舞蹈》进行现代化翻译的话,完全可以用我去看张艺兴的敦煌话剧作为开篇,一位传统的历史学家指责我作为古典学者跑去坐在狂呼的女粉丝中间观看韩国娱乐系统出身的艺人表演的话剧。作为回应,我强调张艺兴话剧里对敦煌历史和敦煌学发展的介绍是严肃的文化呈现,最后那位历史学家被我说服,要求下次话剧演出时带上他。